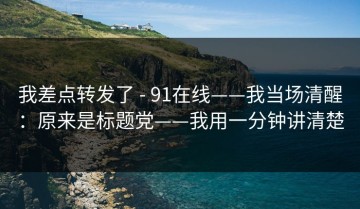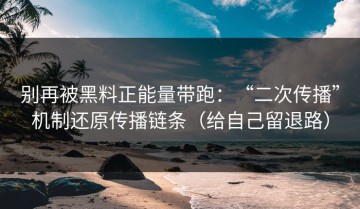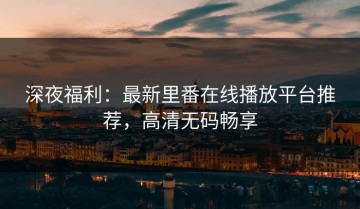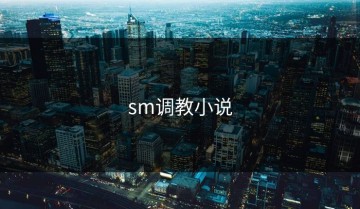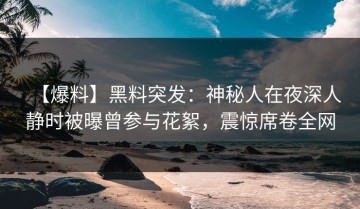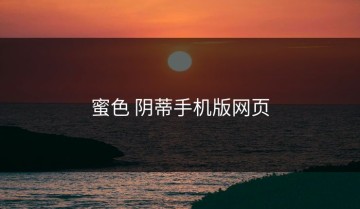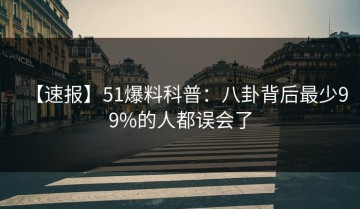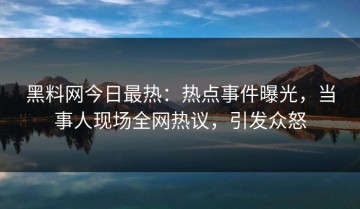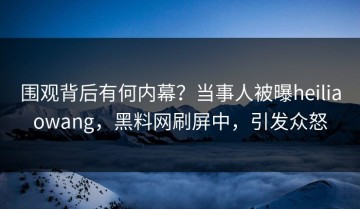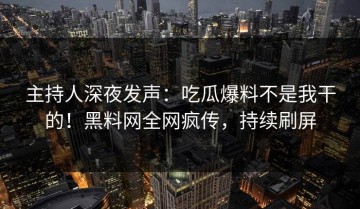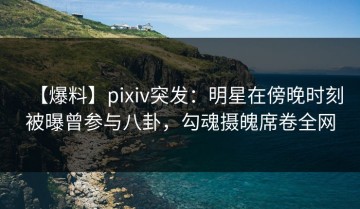黄子华,这个名字在香港文化圈里几乎是信仰般的存在。有人说,他是喜剧演员,也有人说,他是哲学家——但他自己可能觉得,自己只是一个很擅长在舞台上“讲废话”的人。可如果你真的坐在台下,听完他一整场《栋笃笑2011》,你会发现,这所谓的“废话”,其实比很多大道理都更真、更狠、更让人笑到不能呼吸。

2011年是一个微妙的年份。香港社会的气氛、娱乐圈的变化,都让人觉得有点浮躁。黄子华在这个时候,把舞台变成一面镜子,用笑话去折射现实的锋利。开场,他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花哨的特效——就是他一个人,一支话筒,一套西装,外加那种只有他才有的、带着冷笑的眼神。
观众一开始还在等“笑点”,结果黄子华先甩出来的,是一记比刀还快的观察:“做人最怕的不是你没钱,是你以为自己有钱。”台下的笑声,夹着一点被戳到痛处的心虚。
《栋笃笑2011》的主题并不轻松,他谈工作,谈爱情,谈梦想,甚至谈死亡,但全都用最黄子华式的方式包装——先把你逗到缺氧,然后在你笑得最放松的时候,突然追问一个你没准备好的问题。比如那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:“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等机会,其实机会一直在敲门,只是他们一直在厕所里。
”这种隐喻,在香港快节奏的文化里,像一针让人睁眼的古柠檬汁,酸得直击灵魂。
这一场脱口秀背后的魅力,还在于黄子华的节奏感。他不像有些喜剧演员那样依赖密集的笑点,他会慢慢铺陈,用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垒起来,忽然在最高处给你一个关乎世界观的转折。观众在他的语言漩涡里,不知不觉就从搞笑的小故事被带进了哲学的胡同。有人说,看黄子华的演出就像在听朋友讲八卦,但突然八卦的主角变成了你自己,而且被剖析得一清二楚。
将近一个小时的演出里,他把香港人的生活一层一层抽丝剥茧:地铁上的冷漠、职场里的假笑、感情上的互相试探——这些都被他用夸张却精准的表演还原出来。有些片段观众笑着笑着就沉默了,因为那不只是“黄子华笑话”,那是他们自己的样子。
《栋笃笑2011》不同于过去几年的表演,这一年的黄子华更直接、更犀利。他不怕得罪人,因为他知道,真正怕得罪的,是自己不敢说真话那一刻。他用港式幽默的方式,为观众划了一道清晰的界线:笑可以很大声,但心要很清醒。
如果说《栋笃笑2011》的前半段是一场愉快的语言游戏,那么后半段则像是黄子华对这个时代的情书——只不过这封情书带着讽刺、带着反问,也带着解决不了的迷惘。
他谈爱情,完全不走温情路线。他说,“很多情侣都会说,‘我们很合适’,其实合适只是懒得分手。”这一句在台上炸开,笑声、掌声和几个明显的无声反应混在一起。黄子华懂,他不是为了制造争议,而是为了让人正视问题:我们到底是在爱,还是在习惯一个人?在他的嘴里,爱情不是完美的剧本,而是充满漏洞的即兴秀。
《栋笃笑2011》中一些段落甚至让人觉得这是社会新闻的另一种呈现。他谈年轻人的压力,用夸张的肢体模仿面试中的卑微姿态;谈媒体时,他用假正经的语气嘲讽那些为了点击量不择手段的报道;谈人性时,他会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瞬间击穿你对自己的认知。黄子华的舞台,不只是舞台,它是一个让人卸下防备的心理手术室。
在尾声,黄子华收回了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笑话,点题一句:“笑,其实是对绝望最自然的反击。”台下顿了一秒,然后爆发出整场最大的掌声和欢呼。这一刻你会明白,他的栋笃笑不只是让你笑那么简单,而是在用笑替你撑住某种你自己撑不住的东西。
有人看完《栋笃笑2011》以后说,这是一场“救命的演出”。因为它让你在失落、焦虑甚至有点灰暗的心情里,找到一条安全的呼吸通道。你可以在黄子华的段子里看到荒诞,但也可以在荒诞背后看到真心。这种平衡,是很多喜剧演员无法掌握的:太沉重会失去娱乐性,太轻浮又没有意义。
而黄子华的厉害就在于,他能用一段看似随口的废话,把两者都抓住。
黄子华的栋笃笑已经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,而2011这一年,是其中最尖锐、也最成熟的一次。他不再只是观众的开心果,而是某种意义上的见证人和批评者。每一段笑话背后,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,即使你不想承认,它也在那里。
《栋笃笑2011》是黄子华个人创作的高峰,也是香港文化的一次记忆。很多年后再回看,你会发现,那些关于人性、关于社会、关于自我认知的台词依然成立。它没有被岁月冲淡,因为它说出的,不是昨天的笑话,而是今天依然存在的问题。
有观众说,看这场演出的时候,脑子和心是同时被按下了快门——照片里有笑容,但笑容背后,有被提醒过的现实。这就是黄子华的力量:他让你笑到流泪,然后在擦泪的时候突然发现,眼泪不是为了伤心,而是为了感谢自己还活得清醒。